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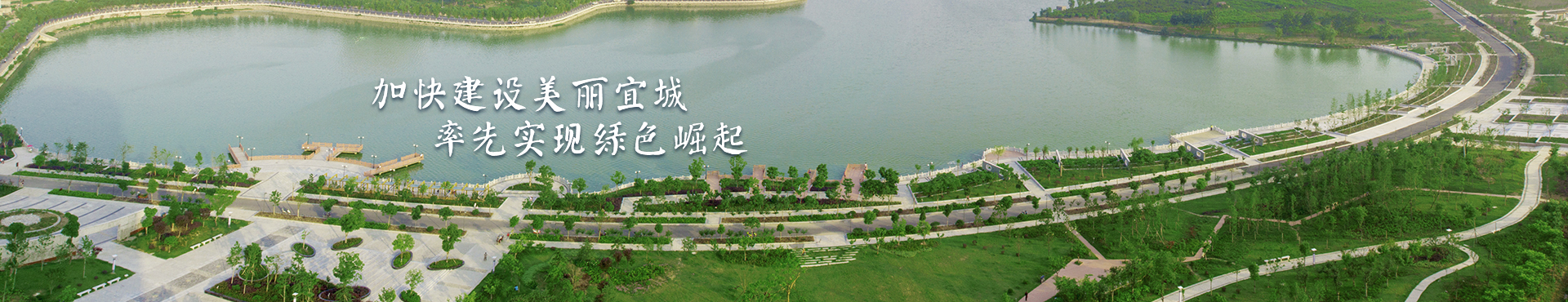
楚蛮与楚国公族族源不同。楚蛮的族源属南方苗蛮系统,为古三苗的后裔,而楚国公族的族源属中原华夏系统,是声名显赫的祝融后裔。二者出现的时代也不同,楚蛮始见于夏商之际,楚公族为芈姓,始于季连,而季连的年代当在夏代之前。
楚蛮与楚国大小不同。初期的楚国很小,楚国初封时是“封以子男之田”,其封地大小,诸书皆言仅五十里,《史记》卷 47《孔子世家》载楚令尹子西曰:“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卷 14《十二诸侯年表》则称:“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至春秋早期,楚地尚“土不过同”(方百里为一同)。而楚蛮早在商代时在南方就有广泛的分布,是南方土著居民中数量较多、分布较广的一支。
与周的关系不同。楚是周朝的封国,而楚蛮则往往成为周朝的征伐对象,周昭王曾大举南征荆蛮。但楚蛮与楚国又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甚至密切到二者难以区分的程度。楚国初封时就是在“楚蛮之地”,到西周晚期时,熊渠统治下的楚国“甚得江汉间民和”,其活动范围“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从熊渠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来看,此时楚人当已植根于江汉蛮夷之中,与楚蛮初步融为一体。到春秋早期时,“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此后随着楚国的发展,楚蛮完全融入楚国,成为楚国下层民众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主体。而楚国之所以能在春秋时期迅速崛起,被时人目为“天方授楚”,当是楚国在长期经营的基础上将楚蛮、濮等江汉蛮族整合成为楚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得楚国迅速摆脱了部落国家的狭隘性质,成为具有地域性质的新型国家,从而具备了强大的实力,令周朝诸侯望而生畏。
由此看来,由于芈姓楚国长期与楚蛮共处,双方当在文化上较为接近。至迟西周晚期熊渠的时代,楚国与楚蛮已初步融为一体,此时的楚国与楚蛮在文化上可能已很难区分。楚国统治楚蛮,属于那种“从深化人民出去,跑到浅化人民中间去作首领”。由古今中外的例证来看,凡少数的“深化人民”统治多数的“浅化人民”而建国者,虽然少数的“深化人民”在政治上起着主导作用,但在生活习俗上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多数的“浅化人民”所同化。芈姓部族虽然在商末周初时主动接受周文化,但其建国于楚蛮之地,不可避免地要受楚蛮影响,西周晚期时又主动与楚蛮打成一片,则楚国在文化上当会受到楚蛮的影响。诚如徐旭生先生所说:“祝融由于到苗蛮集团中做首领,苗蛮自然受他的影响,而他及他的后人的风俗习惯大部分也要同化于苗蛮,也是一种不可免的情形。”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楚文化应是楚蛮及其它江汉土著民族和包括楚国在内的南土诸国共同创造的文化,楚蛮则可能是创造这一考古学文化的主体族群之一,而楚国则是这一考古学文化的主要继承者。
地址:宜城市融媒体中心(宜城大道39号) 邮编:441400
联系电话:0710-4221100 360网站安全检测平台
工信部备案编号:鄂ICP备20009678号-1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登记备案号:鄂新网备0304号

清廉宜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