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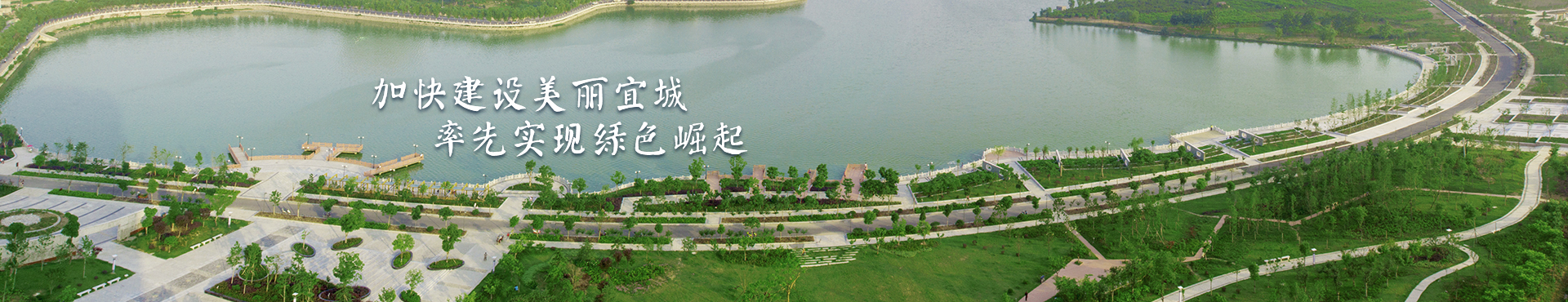
何志汉
八:宋玉的大部分作品,不是写于他在朝任职时的鄢郢和纪郢,而是他失职多年后在异地所写。
辩:“大部分作品”是多少?宋玉传世的作品一说是14篇,一说是16篇,《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宋玉赋十六篇。”那就按16篇算吧,10篇算不算其中的“大部分”?那我们就列出10篇来一一分析。
1、《大言赋》。此赋文的开篇,宋玉自己就把地点给点出来了:“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这个地点就是“阳云之台”。“阳云之台”就是阳云台,也即阳台。《寰宇记》卷148“巫山县”辞条标明:阳云台“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长江。楚宋玉赋云‘游阳云之台,望高唐之观,即此也。’”商务印书馆1931年初版、1982年重印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阳云台”辞条标明:“阳云台,一名阳台,在四川巫山县阳台山上。”于此可见,阳云台在四川巫山县无疑。巫山县在楚时属于巫郡。《史记•楚世家》载:“十九年(楚襄王19年,公元前280年——笔者注),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於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史记》记载得明明白白,不但楚襄王22年(公元前277年),楚国的巫郡、黔中郡都已被秦攻取、归入了秦国的版图,就连经营了数百年的楚郢都(纪郢)亦在此前被攻陷,楚襄王早逃往陈城保命,此后绝无可能去游敌占区的阳云台,当然,此后也绝无可能有宋玉写《大言赋》之事。楚襄王铁定只能在公元前278年郢都失陷前去游阳云台,宋玉也铁定只能在公元前278年前写出《大言赋》,而其写作的地点只能在游览地和鄢、纪两郢都及其附近。《大言赋》是即兴创作之文,最大的可能是襄王和宋玉等文学侍臣即兴比大言后,由一旁的侍从记录下来、或由宋玉自己记录整理成文,存档传世,那么,写作的地点也就在巫山阳云台了。
2、《小言赋》。这个勿须赘言,《小言赋》是紧接着《大言赋》之后,君臣竞比小言而成文,是同日、同时的产物,写作时间当然只能是公元前278年以前,地点就在巫山阳云台或在尚未失陷的鄢、纪二都整理成文。
3、《风赋》。感谢宋玉,他也许是写作习惯,也许是担心后人纠纷,此赋一开篇,他就有交代:“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这里,宋玉不仅把写作的年代和地点交待得相当清楚,连季节也交待了。地点是“兰台”,这个兰台,198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解释说:兰台,“战国楚台名。传说故址在今湖北钟祥县东。”楚辞赋研究专家吴广平先生经过考证,2001年在其由岳麓书社出版的《宋玉集》一书中《风赋》一文的下注里说:“兰台:楚国宫苑名,旧址在今湖北省钟祥县。”这样,兰台就可定位在现今钟祥县的地盘了。写《风赋》的年代呢?应是楚襄王在鄢、纪两都当政时,即公元前278年以前,因为此后紧邻鄢、纪两都的兰台亦同两都一起沦为秦地,楚王再无缘去游。写《风赋》的季节则明显是夏季,气候较闷热,所以当“有风飒然而至”时,楚王才“披襟而当之”,还乐呼“快哉此风!”有人说,《风赋》是若干年后,宋玉失职离开朝廷所写——这绝不可能:像《风赋》这种对问体也是即兴创作的文章,又是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只会及时整理成文,哪会等到若干年后,再去慢慢回忆呢?
4、《高唐赋》。此赋一下笔,宋玉也是先交代:“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这里交代的地址是“云梦之台”和“高唐之观”。“云梦之台”即云梦台,是楚国云梦泽中的高台。《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云梦泽“在湖北安陆县南,本二泽,合称曰云梦”。云梦泽虽然相当大,是梦国的大泽,跨长江南北,云梦台可能也不止一处,然而,在“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就把位置局限得小而具体了,因为这个“高唐之观”(就是高唐观),光绪《巫山县志》卷三十《古迹志》里指明:“高唐观,在县城外西山顶,宋玉赋高唐即此。”高唐贴近巫山,才得以观其上的朝云暮雨。《高唐赋》这个游历文学作品,应是在这里产生。至于开篇的“昔者”二字,给人的感觉是在回顾以前的事,似在游历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才写成的“回忆录”。然而,只要细读全文,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回忆录”若干年后是写不出来的。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文字,而是有着骈散结合的句式、回环和谐的声律、讲究平仄对仗、更讲究身临其境之感受的赋体文学。作为“赋家之圣”、作赋高手的宋玉,当时随王出游,触景生情,才思涌动,出口成章,于旁人或有登天之难,于这位赋圣确是寻常之举,不然,楚襄王又何以任他为文学侍臣?如果是时过境迁、斗转星移、甚至国都沦陷、楚国成了秦的眼中钉从而屡遭重创、到了朝不保夕的份上,宋玉还会兴趣昂扬地写出这种歌赞楚国山川胜景的美文、而且还是回忆着从零开始地写吗?不会的!此时他只会有伤春、悲秋的份了。所以,这个《高唐赋》,即使不是当时成文,也是被以初稿的形式记录下来,事后——也许数日、数月、数年之后,但绝不会是鄢、纪沦陷、家国破碎之后——宋玉将旧作整理后面世。面世时,当初君臣游高唐已成昔往,当然开篇就有“昔者”之说了。这个“昔”字之义,远可溯及十年、二十年、远古,近则可表数日前、昨天。这里的“昔者”,当作近期看待。
5、《神女赋》。此赋既然和《高唐赋》是姊妹篇,内容又相互衔接,所记之事基本上发生在同一时段,所以其写作的地点及时间,应大致相同。即:地点应是云楚泽中贴近巫山的高唐观,应是当时速记出草稿,事后整理成文;时间应是两都未陷之前。
6、《对楚王问》。楚襄王听信谗言责问宋玉有不好的行为,宋玉面对楚王之问,来了一段雄辩,这就诞生了《对楚王问》。雄辩在运用比兴之法时,有“客有歌于郢中者”和“国中属而和者”等句子。其中的“郢中”和“国中”便是地点了。无庸引经据典,“郢中”和“国中”都无可争议地指的是国都——即楚国的纪郢(今湖北荆州)或鄢郢(今湖北宜城)。虽然楚国从丹阳南下后曾四建其都,首迁鄢郢、次迁纪郢,再迁陈郢,终迁寿郢,但其兴旺发达、自认为是太平盛世的时段,还是鄢郢、纪郢时期。其中鄢郢立都180余年,纪郢立都200余年,这两都相继于公元前279年和278年沦陷,此后,楚国的“太平盛世”便宣告完结,国势每况愈下。迁陈郢后仅立都25年又因畏秦而临时迁都到巨阳;再由巨阳东迁寿春(寿郢),此时楚国外患内斗更剧,在寿郢立都才18年便被秦所灭。自陈郢往后,乃楚的苟延残喘、朝不保夕之日,哪里还有歌舞升平?而宋玉《对楚王问》中所描述的“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的歌场盛况,是只有在国家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的环境里才会有的。即使宋玉是追述以往的事,也不会在国运衰微时去津津乐道昔日那些一去不返的风光。由此可知,《对楚王问》只能诞生在楚的鄢、纪两都未陷的公元前278年以前,即楚顷襄王21年以前。写作地点当然也得跟着时间走,才两、三百字的短文,在哪里发生的,在哪里就写了;他是在国都对应楚王问的,在国都也就成文了。
7、《登徒子好色赋》。此篇前面论及太多,只能诞生在鄢郢、纪郢和宋玉的家乡鄢邑未陷之时,无庸再赘述。
8、《招魂》。前面也已述及,此篇宋玉说得太清楚了,宋玉要把楚王的魂招回到哪里?是回到“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宎厦,夏室寒些……”的地方,这种王宫深殿、豪华居所、人间仙境,只有分别建都二百年左右、久久为功的鄢、纪之都才有,仓皇败逃暂栖身的陈郢和内外交困、濒临绝境的寿郢,焉能有之?楚王是去江南的梦泽打猎受惊丢了魂,陈郢远在北方,不仅距梦泽千里迢迢,中间隔着长江天险,还隔着大片的敌占区,甚至梦泽这个旧日的猎场也早被秦占,襄王迁都陈郢后才去梦泽打猎,根本说不通。因此,宋玉就是在鄢郢、纪郢未失时写的《招魂》,再清楚不过。
9、《讽赋》。“楚襄王时,宋玉休归。”——让宋玉自己来澄清史实,真是如鱼得水!一开篇,宋玉自己就把时间说得很准,是“楚襄王时”。楚襄王是公元前298年到公元前263年在位,历时36年,《讽赋》应是在这36年内所作;“宋玉休归”,又把时间说得更具体了,他“休归”自然是朝廷给他探亲假,让他回家,他的家在鄢邑,而鄢邑是公元前279年被秦国占领的,那他作为楚国朝廷的公职人员,来去自由的“休归”又“休还”,就只能是在公元前279年以前,即楚襄王20年以前。——一切明明白白,《讽赋》是写于宋玉在朝廷任职的时候,写于鄢、纪未沦陷即公元前279年以前,写于他休还回朝之际。
10、《舞赋》。还是得听宋玉的。《舞赋》一开头,宋玉又说:“楚襄王既游云梦,将置酒宴饮。”云梦既贴近鄢、纪两都,又是物丰林茂、景致佳好的沃野,是楚国的“风水宝地”。所以楚王常到云梦游猎、观光。云楚泽中为楚王建造的行宫、台观自不会少。然而,这么好的风水宝地,“虎狼之国”的秦国焉能不垂涎三尺?所以,那个令楚国君臣痛心疾首的日子就来临了——公元前的279年和278年,秦国的“战神”白起领兵大举攻楚,不但云梦泽归了老秦,连楚国经营了数百年的大本营鄢都和纪都,都易主他人;还连江南的洞庭五渚,也被人家捎带掠去;甚至还连楚国的先王也不得“安寝”,墓园被人家焚毁殆尽;如丧家之犬的楚襄王仓皇逃到陈地保命。此后,他若还想再游云梦,只能是妄想了——只怕妄想也不会有,只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了!而《舞赋》中描写的“楚襄王既游云梦,将置酒宴饮”,这是何等气派!楚襄王领着一班臣子和侍从,浩浩荡荡,人欢马叫,玩够赏够大饱眼福之后,还要大饱口福,于是便在一处行宫或王家馆驿,大摆酒宴,还要宋玉作赋添兴。这种大胃口的兴头,必定产生在庄辛警告楚襄王“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战国策•楚策四》)之前,而不会产生在两都失陷、襄王接受惨重的教训、采纳庄辛的“亡羊补牢”建议、从此力戒玩兴之后。至此,《舞赋》的写作时间和地点,已不言自明。
——已经举出10例了,还能举:
譬如一,宋玉的代表作《九辩》。此文写作时间较晚,应是写于宋玉失职离朝之后,但其离朝却不可能离得太远,就是不会离陈郢或寿郢太远,就是“去乡离家”也不能离国都太远,以便“愿一见兮道余意”,向楚王面谏;谁知“车既驾兮朅而归,不得见兮心伤悲”,“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失职一悲,再不能面君相谏、施展抱负,更增其悲,这才使其“悲秋”的情结如潮水般涌来,遂成就千古名作《九辩》。所以,《九辩》的写作时间应是宋玉离职后,写作地点应是其“羁旅而无友生”的异乡,但这个异乡不会是在千里迢迢的地方,这才合情合理。因为既然“去乡离家”是为了面君,却无端地跑到一个比家到国都更远的地方呆着,然后累死马地往返傻跑,这不但不是宋玉,连一个有着正常头脑的普通人也不是!
譬如二,《钓赋》。虽然没准确交代时间、地点,但其时间、地点已隐含其中,因为既然文中反映了楚襄王对钓鱼兴趣浓厚,不厌其详、打破沙锅问到底地向登徒子、宋玉了解钓术,那么这个时间段就一目了然了:事情和文章应是产生于楚国鄢、纪两都未失,楚王“不顾国政”、贪图游乐、醉心渔猎的毛病未改、还没有接受庄辛的诤谏而决计“亡羊补牢”之时。
譬如三,《御赋》。此赋与《钓赋》内容非常相似,应是与《钓赋》创作时间和地点接近的作品。
譬如四,《高唐对》。此赋只是《高唐赋》前一部分的异文,理当和《高唐赋》一视同仁。
譬如五,《郢中对》。此文又是《对楚王问》的异文,其创作时间和地点,又岂能与《对楚王问》有多大差别吗?!
——连举带加,已经将宋玉作品举出15例了。这15例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他的这些文章的创作时间,大都是他在朝廷(即鄢、纪两都)任职时,创作地点或在出行的目的地,或就在都城。
有人说,宋玉的大部分作品不是写于他在朝廷任职时的鄢、纪两都及其附近,而是别的什么地方。笔者认为这样说实在找不出根据。宋玉传世的16篇作品,总共才12000多字,如果去掉后人加上去的标点符号,就只有万把字了。如果这万把字的大部分都不是他在朝廷时所作,而是他失职后流落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所写,那他在朝中就没有写什么东西了!?那他这个“文学侍从”还称职吗!?如果无视史籍记载的、特别是宋玉自己在作品中交代清楚了的史实,而随意造一个说法,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因而也是不可取的。
地址:宜城市融媒体中心(宜城大道39号) 邮编:441400
联系电话:0710-4221100 360网站安全检测平台
工信部备案编号:鄂ICP备20009678号-1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登记备案号:鄂新网备0304号

清廉宜城